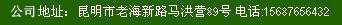|
(作者种植的盆景) 光都照在我们身上 作者:王雄 (一) “作家,你看大家都卖得不错,就你不行啊,没怎么卖。卖来卖去都是几个文友。要多向大个儿学习啊,他这个月卖了万把块。要是你每个月也卖个万把块,走起路来还不是这个样子……”村夫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裂瘸着身子把左腿抬得老高然后放下,再抬起右腿,同样老高,放下后再抬起左腿,如此反复好几次慢动作:“吊得很……”整个身子像一株被“拿弯”的盆景主杆,配合着双腿舞动起来的双手是“片”和“飘”,合不拢的嘴里笑呵呵地咂着一支烟,昂着头冒出的缕缕青烟是可“变换”的“顶”。烟头的火光处在一盏聚光灯的正下方,仿佛香烟是被它给点燃的。十年如一日。教授总在村夫生日当天请我们一起吃个饭。我们是一群“盆友”。喜欢盆景的朋友。当初,我想请大家吃个饭,尤其是想请村夫,于是建了个群,成了群主。村夫将群命名为“沙洋几个玩泥巴滴”。教授刚喜得贵子,在不惑的年纪。坐月子的教授夫人在我进门后递上了一杯热茶。在厨房里忙碌的是一位之前并没有见过的小伙。我不是第一个到,也不是最后。我们在原沙洋汉江中学靠最西边的那栋宿舍楼的院子里落座。曾经热闹的宿舍楼,现在是教授一家人的“独家大院”。在此之前的九年时间里,是他一个人的独家大院。院子的水泥地面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教授的盆景素材。同样大小的凑在一起,纵向、横向拉扯着的绿色尼龙细绳隐约可见,它们是当初摆放这些塑料盆的参考依据。与这些地面素材相互辉映的是另外摆放在宿舍楼三楼楼顶的几百盆盆景。教授是在我到后不久回的家。依然留着两边剃光光,中间一簪长毛的发型。走的同样是后门。大门管着整个大院,在进到大门约两米远的位置,堆满了黄土、风化石、腐叶土、煤渣的混合物。混合物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抄匀之后便成了培育盆景所需的泥巴。教授到后跟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后港的课上完就往回赶!”说完习惯性地用右手把镜框往上推了推,俨然一个斯文书生,全然不是那个玩泥巴的人。紧接着从裤兜里掏出烟来发给我们。除了我,大家都各自掏出火机点烟,一张张熟悉的脸在腾然而起的烟雾中瞬间清晰呈现。仿佛我们的上一次相聚就在昨天。教授是原汉江中学的老师,几年前汉江中学合并到现在的沙洋职高,他跟着到了职高。最初教的是数学,进修音乐之后成了专职音乐老师。他的一位同行兼朋友说:“我们的课都可以找其他老师代哈,唯独他的课别个代不了……”没结婚的前几年,他在金水湾开了个音乐培训中心。结婚后又在汉上小学和后港镇上分别开了两个培训中心。晚餐,推杯换盏自然必不可少。席间说的都是盆景之外的话题。集中聚焦在一个新生儿的诞生与其母亲之间的种种密切联系,以及对母爱的种种敬畏和感动。教授谈及儿子黄疸偏高,需要紫外线灯光照射治疗时,将香烟深吸一口,吐出浓浓的烟雾,微弱的火光照亮他整个的脸庞,说:“如果儿子在旁边,但然是不敢抽的!”晚餐结束后的品茶时间,才是我们讨论盆景的惬意时光。边参观边交流是共性习惯,教授手持一支强光手电,从这头照向那头,隐匿在茫茫黑夜之中的众多好东西都被点亮。我们顺着他光柱的指引再一次感受到他的精心规划:对接白蜡、金弹子、老鸦柿、朴树、榆树、刺冬青和三角枫分区分片地隐没在夜气之中,被夜露濡湿了叶子。此刻的手电是他手里的一只粉笔,素材分区的条块是他熟悉且喜爱的琴键。今夜无月,热烈的光线穿透夜色,次第洒在叶片之上。教授挥动的手电最后落在了院子边上宿舍楼的三楼楼顶边缘:“各位还要不要去三楼看看?”“要去你们去吧!我的腿脚不方便,这楼梯又比普通的陡,就不上去了!”村夫说到。其实,楼顶的那些盆景我们都见过很多次,他这么一说我们也就都放弃了上楼的打算。“估计你三楼的都成精品,还有没有五百棵?……”村夫的夫人接着村夫的话说到。“精品谈不上,完全是按着自己的感觉弄的。棵是没有了。棵还是有的……”教授说。“那也就是说有棵已经卖出去变成了钱。这多年了,我想着你跟村夫当初一起买的个对接桩也不可能还有个……”村夫夫人道。在我的印象里,教授三楼的盆景桩一直都是铺满整个楼顶的,从来没有减少过。直到近两年自己弄了个盆景园之后,才慢慢领悟到:同一个地方可以勉强容纳盆盆景,也可以只容纳盆。密与疏之间微妙关系,外行人看不出来,内行人看在眼里却不说出来,不是特别精妙的盆景,从不问其去向。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几年之后,只剩盆、盆同样都是可以摆满整个楼顶的。聚光灯吊在一长形的简易遮阳棚下。棚不大,刚好容下我们喝茶。废弃的喷绘布是棚顶。顶起棚顶靠西边的铁柱上,一根手臂粗细的紫藤已悄然攀上棚顶。聆听着我们来或者不来,棚下所有的动静。棚顶的正上方是厨房,厨房的两边是卫生间跟客厅。客厅往下走几步台阶穿过中堂再迂回是卧室。把这些地点、方位在脑海里立体地过一遍,就是一件成熟盆景作品的生命“水线”。我们不是在客厅里吃的饭,在院子边上那三层宿舍楼最南边、最角落里的一间房里吃。显然,这间房是被改造过的。只要是能被利用上的房间跟场地都是被改造过的。教授料定这荒废的校园,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将成为政府或者开发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再利用资源。有时候荒废就是最大的安全。至于这安全的期限有多长,谁也说不准。教授在别处另购了房产,并进行了装修,以防安全期限随时结束。我们问及什么时候请我们喝乔迁之喜的酒,他说到了时间自然会说。十年如一日的旧居其舒适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远远胜过新居的新鲜感。况且,教授还在院子边上的废弃仓库里,养了只土鸡,每天都有新鲜的土鸡蛋出炉。在喧闹的城市一隅有一处世外桃源的居住地,怕是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事情吧。如果一定要把这惬意时光限定一个期限的话,教授希望是一万年。虽然自己对香火的延续是那么的渴望,一向慎重的他还是在四十岁才喜得贵子,为一个五世同堂的大家族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而在他与我们讨论怎么把紫藤运到新居三楼的时候,我们似乎又嗅到了某种变化的气息。因势而变不正是盆景人的追求么?(二) 大个儿跟村夫接触的最早。十多年前,他有一台大货车,经常给沙洋的老板们拖米、拖水果到秭归、巴东一带卖,顺便带着村夫,一路陪聊驱散瞌睡。说是卖米、卖水果其实是用米、苹果换取橙子。用沙洋产的大米筛出来的碎米、陕西运过来的快烂掉的次品苹果换秭归、巴东特产的橙子。那个时候,温家宝总理还没有为秭归脐橙代言,橙子的价格在本地根本卖不起价格来。只要说起这段往事,村夫就会讲:“沙洋的老板心黑,烂米、烂苹果也就罢了,在交换的时候还小气得很,用很少的米和苹果换很多的橙子。有一次,有位大肚子的孕妇背了一背篓加一蛇皮袋子橙子来换苹果,结果换了半背篓烂苹果。我实在看不过去,就从袋子里多拿了几个给她……”这个故事,我听了不下十遍。秭归、巴东是我的故乡,孕妇每天吃橙子吃腻了,换苹果是想换个口味。那时的交通不便,孕妇可能是从山顶把橙子背下来的,毕竟可以通大货车的公路一般都是沿江而建的。她也是想多换点苹果回去的,一背篓加一蛇皮袋子在她看来是足够多的。只是这场交易的规则都是对方说了算,她除了被动地接受之外,并无他法。也或许她早已悉闻这不平等的交易,那个时代那样的交易年年都有,几年下来,峡江的村民们也都习以为常。故事之外村夫强调的是:他对于孕妇是同情的,对沙洋老板是憎恶的。听得次数多了,也就从中感悟到:他其实是对沙洋老板对待一个新生命的“无动于衷”而愤青。那时候,他的年纪刚好跟现在的我差不多。村夫不可能像多给孕妇苹果那样给所有的村民们都多给,他不是老板,他只是老板请的司机的一个陪同。陪同在多给孕妇苹果的同时,发现了许多可以用来制作盆景的素材。用他的话说是发现了新生命。他老说:“山采的素材一辈子都在大山里,能有什么作为?只有挖回来经过培育、造型,最后上盆成景才能让它价值最大化。”在他的眼里,每一棵山采素材都是一个新生命。起初,村夫只是用随身携带的简易工具,把随行遇到的较好的素材挖起来顺便带回沙洋,占据的只是大货车的某个小角落,整个的货箱满载的都是峡江的橙子,与来的时候烂大米、烂苹果所占的空间相比,橙子所占的空间几乎多出了一倍。而且这橙子一旦被运到沙洋,其价值也将翻几番。当然,这些都是村夫顺便告诉我的。顺便的次数多了,村夫便萌发了到峡江收购素材的想法,于是请大个儿帮忙运输。大个儿原本对盆景是不感冒的,帮忙运输的时间久了,慢慢也爱上了盆景。帮村夫运输的同时,自己也顺带收购一些素材,与村夫不同的是,他的素材不是栽在盆里,而是栽在地里。没跑大货车之后,因为儿子在杭州成了家,爱人要帮忙带孙子,大个儿便去杭州开了好几年的士。几年下来,有些素材去了“西天”,有些素材给养“骠”(废的意思)了,当然也还有一小部分成了精品的“前身”。在大个儿的父亲把一棵几近成型的多杆丛林大紫薇桩,一杆一杆地劈开单独下地放养的事件发生之后,大个儿突然间觉得是时候回去管管那些盆景素材了。大个儿回来之后圈了十几亩地办起了养猪场。那些盆景素材就在猪场的房前屋后,不说猪粪对这些素材起到了很大的肥效,单是整个围墙内空气中弥漫的猪粪因子都足以促进它们健康地成长。我们每次羡慕他的时候,他就说有空了用他的罐车给我们免费拖几车粪水来给盆景上肥。他许一次,我们就望一次,只是好些年了,也没有盼到。去年,他索性关闭了通过环保认证的猪场,一头猪也没养。彻底断了我们的念想。关闭之后,非洲猪瘟爆发,到后来猪肉涨价,波澜起伏的状态如同他经营猪场这几年的市场行情走势。我们调侃他去年要是继续养,现在可就赚大发了。他说那非洲猪瘟的损失怎么算呢?没亏钱就是最大的赢家。懂得进退,又何尝不是一种安全?大个儿的素材累积到现在可谓是厚积薄发。与他的厚积薄发相对应的是村夫的薄利多销。村夫的园子里只要是稍稍有点型的盆景都是留不住的,他与我们不一样,他是以盆景为生的,我们只是把盆景当爱好。如果说大个儿厚积薄发的那些素材是厚重的,那村夫薄利多销的那些素材就是灵动的。厚重展现的是年功,灵动却是可能升值无限的潜力股。厚重表现的是自然的成长,灵动却是把未来的发展方向做了具体的规划和指引。一个憨厚,一个灵巧。村夫用他的盆景养活了自己一家,培养了大学生女儿。园子是租的林业局多年前苗木基地边上的一亩三分地。前些年苗木行情好的时候,园林局从没收过他的租金,后来行情不好了就把其下放给某位工勤编的工作人员,苗木自行交易但不发工资,自此,这位工作人员开始收村夫的租金。前年,这位工作人员因苗木实在没有了销路,便把苗木地交回了单位,要求单位为其发放工资。单位从不接受到僵持再到被迫接受,一晃就是一年光阴,这一年没有任何人向村夫提及租金的事情。去年,林业局通知村夫苗木地可能改作他用,让他做好搬迁的准备。于是,他在沙洋乃至荆门范围发布园子整体转让的消息。只是在整个沙洋乃至荆门范围,都没有人接盘。这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销售的不稳定,毕竟盆景不是生活必需品。有,可以过,没有,说不定过得更好。村夫的销售从一开始就走的网络。最初是在QQ上卖,在空间发照片;后来在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jingmenzx.com/jmxx/11915.html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辽宁省这4个地方已被国家选中,马上要崛起
- 下一篇文章: 大荆州真不服周,ldquo第四极r